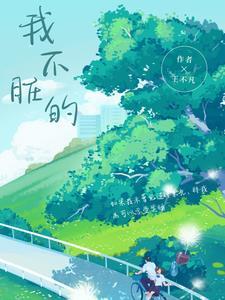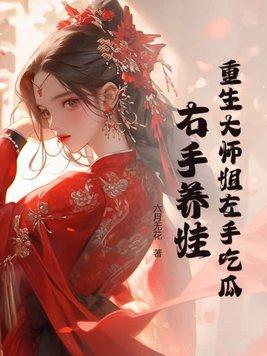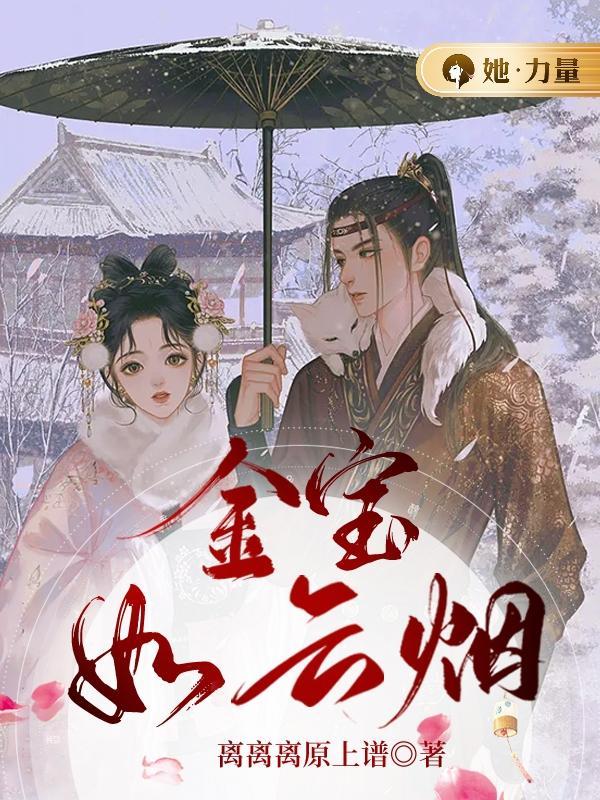最新小说>夫郎他有两幅面孔梨子甜甜 > 第88章(第2页)
第88章(第2页)
商人们憋屈的时候,此刻最高兴的人莫过于许从诚了。
前年他就知道萧娘子新收了徒弟,知晓两人都是女子,又是独居,怕县里有人起歹心,他巡逻的时候都多在这片行走。
遇到宋寒露还是去年端午,萧娘子带她上许家,给他娘裁剪端午衣裳的时候。
那天,他下值早,刚迈进家门,就听到一道俏生生的声音问:“许夫人,你家的灶台在哪儿?”
他娘刚答了一声,一抹粉色的身影从房里钻了出来,奔向他所在的灶台。
因为他娘不做饭,他每日下值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烧水喝,图便利,他爱从偏门回家,因此他娘和屋里的人并不知道他回来了。
宋寒露从屋里钻出来,在灶台跟前扒拉一阵,扒拉到一块合适的木炭,她拿着满意起身,看到灶台前的他愣了愣。
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,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:“借你一根木炭,过后还你。”说完人就跑了。
许从诚当时还在想,一根木炭有什么好还的,没多久,他在街上巡逻。
他们这地儿,冬天都不怎么冷,五月已经热得人汗如雨下了,偏生端午人多,怕街上行人闹事,他们这些巡检一刻也离不得,好死不死,出门带的水也喝光了,正当他渴得都张不开嘴时。
一个小孩出现在他面前,给他递来了一竹筒的冰镇杨梅水:“哥哥,那个姐姐让我给你的。”
他一抬头,长街尽头,宋寒露拿着一支木炭,隔着人海跟他说:“还你的!”
那天的杨梅水是许从诚这辈子喝过最甜,最好喝的杨梅水。
虽说后面两人交集不多,偶尔看见也只是点头之交,但她的身影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他面前。
甚至他巡逻的时候,时不时地走到了萧娘子居住的那条街,期待能够碰到偶尔出门买菜或者逛街的宋寒露,看上一眼。
意识到自己对人家起了心思,许从诚当即回家,让他爹娘上门去提亲。
他爹娘也没反对,十八九岁的年纪正是说亲的好时候,宋寒露家世清白,又自强自立,小小年纪学了一手裁剪的本事。
且人家爹娘愿意女孩子出来学手艺,可见是个有成算有主意的,虽说是乡下人,但比着城里人也不差什么。
备好礼,请了媒婆到宋家去提亲。
只是他们去得不巧,正值过年,又遇到商人们把种云耳的事闹得全县都沸沸扬扬的,去宋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。
他的名册放在中间一点都不显眼。
媒婆当时没得答复,许从诚失望极了,还以为宋家没看上他,这桩婚事成不了。
没想到峰回路转,过完年,媒婆上门回复,说宋家那边让他们上门去商议婚事。
许从诚知道这个消息,高兴得吃饭嘴角都是咧着笑的,最后要不是他爹踹了他一脚:“没出息,还不快去好好准备,别在你未来岳家面前丢脸,把婚事搅了。”
他才强行镇定下来。
本以为,去宋家提亲的人多,且又是嫁女,宋家父母,甚至宋家哥哥怎么都要刁难一番。
谁知道,宋家人出奇的好说话,到了宋家一点刁难都没有,只是问他们:“寒露的婚期,可不可以定在寒露出师后。”
女孩子学个手艺不容易,现在成婚了,学到一半的手艺多半要荒废了,他们舍不得。
许从诚自无不可,他现在还年轻,晚两年成婚也没什么,先把婚事定下再说!
“……”
送走许家人,宋惊蛰松了一口气:“没想到这许家还挺好说话的。”
他先前以为许父好歹是个从九品的官,要拿一点官架子的。
谁知道人家为人可随和了,一到宋家,就是宋大哥宋大嫂地称呼他爹娘,对着他和立夏也和颜悦色。连他们的女儿手上都被塞了一对铃铛手镯。
许母就更不用说了,一进到宋家家门就拉着郑月娥说她把寒露生得多么好,她有多喜欢,现在两家能结成一家,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相看相看,看的就是人家父母的态度,要是婚前他们都表现得不耐烦,更遑论婚后了。
人家父母态度做得这么足,宋惊蛰也不好再说什么丧气话。
林立夏笑他:“你就是太紧张了。”
宋惊蛰也不否认:“现在我们家不一样了,我总怕遇到些不好的人家,害了寒露一辈子。”
女子哥儿嫁人犹如二次投胎,像葛晓霜,她成婚前也没想到叶大勇会是那样的人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