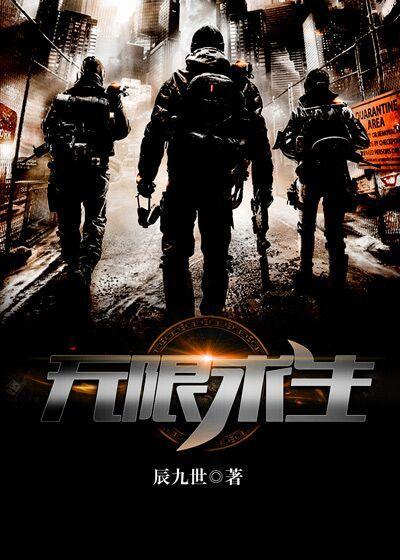最新小说>我才不恋姐呢 > 第80章 含着舌尖的热吻带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痴缠和贪婪(第2页)
第80章 含着舌尖的热吻带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痴缠和贪婪(第2页)
“以後会有机会养的。”她补充道,“德文卷毛猫。”
柳见纯淡淡地笑了笑,她纵容地看虞树棠找了那麽一会儿,见还没找到发圈,就想提醒一句,还没来得及,虞树棠就在夹层里摸到了。
几只发圈,还有一小支漱口水。发圈零散,就是那种最简单的样式,一只黑色,两只混绿色,还有一只浅咖色的小肠发圈。
“姐姐,我拿哪一个?”虞树棠道,“你这儿放了四个,平时用哪个?”
“你去纽约带发圈了吗?”柳见纯道,“全拿走吧,我家里还有很多的,发圈总是一买就是一整包,根本用不完。”
虞树棠有点雀跃地嗯了一声,她拉开随身的双肩包,把发圈放到最里头的夹层里,把给自己那只一号盲盒也放了进去,这样就不用姐姐一直提着了。
拉上拉链之前,她犹豫了一秒钟,又把那个简单的黑色发圈取出来套在腕上,自言自语道,也不知道是讲给谁听的:“一会儿扎上吧,登机方便。”
她左手腕上是一只日志钢表和一条纤细的宝蓝色四叶草手链,金属美丽,颜色斑斓,这个黑色发圈简直是突兀至极。
柳见纯瞟了一眼,伸手一拉,盘发散开,柔柔地披在她肩头,她把自己正戴着的发圈摘了下来,递给了虞树棠。
那只小肠发圈是种毛茸茸的混色毛线,像一片撒开了的跳跳糖。也不算很合适,但总比乌漆麻黑的好很多。虞树棠满心欢喜的套上,柳见纯还没收回手,催促地用纤细的指尖点了点她的手腕,虞树棠心弦一颤,将那只黑色发圈套到了她的腕上。
明明机场距离不近,虞树棠总觉得在车里的时间还是一闪而逝,她办完值机和托运,柳见纯也到了该走的时候。
“到达之後告诉我一声。”她真想再吻小树一下,只是这里是机场,公共场合,实在不方便。“记得拆盲盒,我也回去就拆。”
“我们可以一起拆吗?”虞树棠立刻说,她早就将时差算得清清楚楚,“我明天七点半到纽约,那时候纽约早晨六点半,纽约八点的时候国内晚上九点,我们可以一起拆。”
柳见纯眉眼弯弯:“好呀,这时间很好,我们应该都有空。”这种培训时间作息肯定都会正常一些,不至于到凌晨才刚刚结束,连觉都睡不成。
“想我就给我打电话。”她按了按虞树棠的纤直的肩膀,将澎湃的热情这样轻轻地按了下去,“我想你的话,也会给你打电话的哦。”
飞机航行一天,本该傍晚落地,却穿越进了清晨。
酒店统一安排在广场酒店,第一天休息,明天才正式开始。套房不算小,卧室浴室,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。她和同一批过来的法尔林申城办公室的同事在同一层,大家约着第二天到时候一起过去,这会儿不是在倒时差,就是在收拾东西。
这间套房要待至少两个月,虞树棠一点不糊弄,每件衣服该挂的挂,该叠的叠,生活用品也各归其位。她用一个小时收拾完,另外半个小时一边看CPA的教材一边盼,八点钟是约定好的,准时毫无疑问也是合格恋人的重要标准,她一秒也不停,直接拨通了电话。
只响了一声,那头就接通了。柳见纯正靠在床头看电子书:“给你们安排的套房条件好好。”虞树棠一到,就给她发了消息,从套房的大窗户望下去,高楼大厦,钢铁森林,几乎有种震撼性的效果。
虞树棠也坐在松软的床上:“姐姐,你现在在看书吗?”她已经有点摸清柳见纯的生活了,非常规律。工作,写东西,做研究,看书。娱乐就是打羽毛球,和朋友出去吃饭,泡汤。
姐姐好像没那麽喜欢骑车。这个发现不仅不让她失落,反而让她心里甜津津的。不喜欢骑车的话,当初为什麽要找她配车呢?她不肯往下想了,这件事像一块很大的糖,她不愿意想清楚,她想永远这样甜蜜地含着睡觉。
“在看《雪落香杉树》,”柳见纯道,“还在等着你和我打电话。”
小树是她谈过的年纪最小的恋人,可竟然也是最守规矩的,约好这个时间,真就一分不差,换成其他人在这个时候,怕是一闲下来就会给她电话了。
她并不觉得失望,因为她感觉得到小树对她的爱,更感觉得到这份拘束下的珍惜。
她听见小树轻微的笑声:“姐姐,那我们拆盲盒吧。”
两个人把手机放在一旁,同时撕开易撕条,柳见纯没注意到虞树棠这边的声音在抽出卡之後就停了,她撕开里面的袋子,惊喜地把可爱的小挂件拿了出来,太阳脑袋的星星人悬挂在一轮橙红色的月亮上,“小树,我的是有你就是晴天。”
虞树棠紧盯着小卡上那一行字,好一会儿,她问道:“姐姐,你们在哪里抽的啊?”
“绢水汤泉。”柳见纯不解其意,“怎麽啦?”
“这个挂件太可爱了,等我回去我们再多抽两个吧。”她将盒子翻到侧面,选了一个寓意好的,“我的是等你的来信。”
“这个也很可爱。”柳见纯笑道,她动了心思,打算真写上一封信,贴上邮票,放到虞树棠家的茶几上。
国内时间不早了,虞树棠又刚到纽约,两人聊了没一会儿,就挂断了电话。
蓝色星星的挂件框架里,她的星星人愁眉苦脸。
虞树棠脸颊绷紧,依然是紧盯着那张小卡片,她抽中的,是心碎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