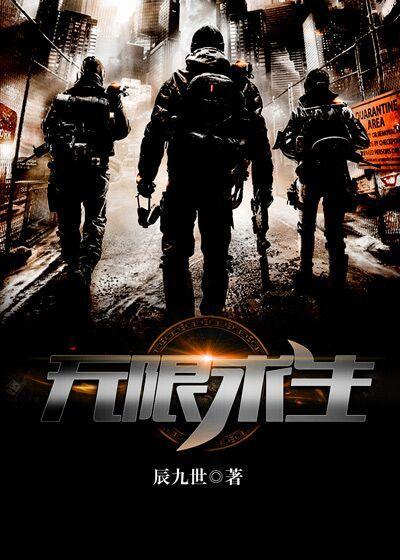最新小说>单于的女儿嫁给狼 > 第十一章 长安风暴(第1页)
第十一章 长安风暴(第1页)
第十一章长安风暴
先皇当政之时,好歹有个嫡长兄的名份在上,胶济王还略为收敛一些。可几年前今上即位後,胶济王成了叔叔,成了天子的长辈,行事更加骄横无忌。不但再无就藩之意,其在长安的府邸整日里冠盖如云,车马喧嚣。朝中许多大臣眼看新君势弱,纷纷投到胶济王门下,以求官位晋升,所谓“烈火烹油”,便是讲如今的胶济王府之势。
可当今天子虽只有二十多岁,但却精明神武,胸怀大志,如何肯被叔王架空,做个傀儡天子?隐忍了好几年,终于看准时机出手了。
俗话说:“十里不同天”,何况关中与塞外千里之遥,更是两重天了。越往南走,春天的气息越浓重。去时不过深秋,归时已是春盛之时,关中处处繁花似锦,官道旁的一株株柳树枝条上喷吐着嫩绿的新芽,在风中摇摆着,仿如女孩们披着绿纱起舞。
眼看已进入高平郡境内,离长安也不过三四百里路程了,顶多再走个两三天也就到了,和亲使团衆人心中顿时松驰下来。都想找个地方打个尖,歇一歇,养养精神。
“道旁有块空地,都歇一歇,洗马的洗马,造饭的造饭吧!”震远伯井邯骑在马上遥遥一指,一声令下。
将士们一声欢呼,冲着道旁的树林空地走去,寂静的树林顿时一片喧嚣之声。当此之时,忽见官道从南望北的方向,缓缓走来了三十馀个衣衫褴褛,蓬首垢面的犯人。在他们身後,是若干名身骑大马的押送军士。
一阵春风吹来,将为首押送军官的斥骂声隐隐送来:“你们这些逆王馀孽,犯了这般十恶不赦的罪,皇上居然还饶你们不死?连累得老子一趟趟往边关送,若依老子说,早他娘一刀一个全宰了干净!”
逆王馀孽?离开长安之时,没听说有哪个王爷造反谋逆呀?怎麽?莫非长安出什麽事了不成?使团衆人心里都犯起了嘀咕,渐渐聚拢了来。
这些犯人年长的是四五十岁,小的只有十二三岁,且个个看上去疲累已极,加上手上捆着绳索,行动十分不便。有一个少年便摔了一跤,连带着绊倒了身後的几个同伴。
“谢眺,一路上就见你不停地摔跤。你他娘的还以为自己是胶济王府里的世孙呢?赶紧起来。”押送武官一边骂,一边就是一马鞭抽来,少年只得一面哭泣一面挣扎着站起。
谢眺?这个名字一落入井飒耳中,他只觉脑中轰地炸开了。这可是他的发小,一起骑马射箭,一起爬树摸鱼,一起上官学挨先生板子的死党啊!会是他吗?那个玉树临风,满身玉佩叮当的王府世孙,怎麽会沦为一个流配犯的?井飒忍不住喊了声:“谢眺!”
谢眺摇摇晃晃站起,当看清叫他的人之後,顿时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,猛地向道旁冲过来,喊里乞求着:“井飒,震远伯爷爷,我是谢眺啊!他们说我大父谋逆,我冤枉啊,你们快救救我,我不要到边关去呀……”
“妈的!”那押送武官断然下马,一脚将少年踹了回去,骂道,“什麽震远伯?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们胶济王府的人!快滚!”
那武官踹完这一脚,戏谑地看了看和亲使团的旗旌一眼,又向井邯投去了蔑视的目光。得意洋洋地骑上马,扬长而去。只有少年谢眺的哭泣声仍在风中久久回荡着……
“大父,这……这是怎麽回事?谢眺怎麽会被流放的?还有他们说的什麽逆王,是指胶济王吗?这……沐阳公主才刚刚为国和亲,怎麽胶济王就谋逆了?”井飒的声音在些颤抖,那是难以抑制的恐惧使然。要知道,胶济王执掌兵权数十年,军中一多半的高级将领都是他提拔的,也包括自己的祖父井邯。
井邯沟壑纵横的脸庞瞬间变得苍老而阴沉,咬牙说道:“啓程,速开往长安!”
从高平往长安的这三四百里很不平静,一路之上不断遇到从长安出发的流放犯,加起来足有上千之数。有胶济王府的亲眷门客,有平日里与胶济王来往过密的朝臣,但更多的是军中将领及其家人,且多是长年在胶济王麾下受其驱使以及由其提拔的中青年将官。更糟糕的是,这些人都与井邯相熟,且交情匪浅,每每在路上邂逅,或见到“震远伯井”的旗帜便呼号求救。井邯无奈,只得收起旗帜,默默前行。
老井邯的脸越来越阴沉,小井飒的心中也越来越忐忑,他已不止一次地问祖父:“大父,咱们回到长安会怎麽样?我会不会也像谢眺那样被流放?”
井邯无言以对,他不知道回到长安将面对什麽,不得不做好最糟糕的打算。目下来看,胶济王被判定谋逆罪名已定,定难逃一死。而自己也难逃一个“附逆”之名,这是最轻的了,但愿有此次送亲之功,也许能换个从轻发落。唉!长安……正在经历一场风暴的长安,等待自己的将是什麽呢?
显陵乃高皇帝长眠之处,距长安不过三十里之遥。长安城绵延数十里的城墙沐浴在金红色的夕照之下,巍巍赫赫,格外壮观。而送亲使团衆人的心中却分外沉重,纵然归心似箭,却谁也不敢贸然入城,齐齐将目光投向震远伯井邯。
“就地先找人家歇宿一晚再说吧。”井邯一声吩咐,衆人开始忙活起来。
一衆人等在镇上一户大财主庄园内住下了。井邯正犹豫着要不要趁着城门未关之际,派人进城找人摸摸情况,不料家中却来人了。
“父亲,我在此处已候了几日了,估摸着你们也该到了。”来人正是井邯次子井攸,时任金吾卫中郎将,也算是天子近卫了。
一见儿子,井邯立即拉他到自己卧寝中,吩咐孙子道:“飒儿,我与你二叔有话要讲,你守在门口,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这间屋子。”
“大父,二叔放心,井飒一步不会离开。”知道他们有机密事要商议,井飒慨然应允道。手持短剑守在房门处,房中二人的谈话也尽入耳中。
二叔井攸先简要概述了胶济王谋反的全部经过。就在沐阳公主出发和亲的当日,皇帝当殿下令嘉许胶济王深明大义,送女和亲。因亲王已是最高爵位,无以为赏,特意嘉封胶济王次子为济国公,世袭罔替。之前的长子因平定淮北之功,已被封公爵位,如今一门父子,一个亲王,两个国公,且都是世袭,堪称富贵无匹。此等喜事,如何不堪一贺?
三日後,胶济王府隆重举办谢宾宴,长安城里有头有脸的都备厚礼上门道贺。宴饮直到天黑时分,朝臣贺客慢慢散去,唯有一些军中党羽将领与核心门客舍人依旧在举杯相庆。就在此时,大祸突然降临——两千精兵突然从天而降,包围了胶济王府。
“长安守军不乏胶济王之部属,这两千精兵从何而来?”井邯问道。
“父亲还记得国舅南宫雍麽?”
“南宫雍?那小子不是领兵镇守淮北,准备随时渡江收复江南的吗?怎麽?他回长安了?”井邯十分惊讶。
“圣上好口风,连左右近侍都不知晓。那南宫雍率领着近万精骑星夜西行,在终南山谷隐蔽三日,再扮作百姓樵夫换装散流入城,重新秘密集结,趁着胶济王府不备之机,突然实施包围。胶济王大怒,亲自率领府中二百名甲士与剑士冲杀突围,可血战两个时辰,也没能迈出前院一步。绝望之下,胶济王只得自刎而死,待得南宫雍攻入府中,其尸依旧伫立血泊之中。”说起这段惊心动魄之事,井攸也是唏嘘不已。
屋中沉默良久,方才听到井邯的一声长叹:“可惜呀!胶济王一生横刀立马,纵横天下,却落得如此下场!那……圣上以谋反罪论处皇叔,可有实证?”虽然胶济王骄横,然毕竟有长辈的名份在,即便是天子,也要拿出实证,才能让天下信服啊!
“有些事,我也是最近隐隐约约才听说的。”井攸压低了声音,“父亲还记得先皇之死麽?”
“先皇之死颇为突然,前一日还好好地上着朝,不想次日便突然暴亡,当时说是得了急症。怎麽?竟与胶济王有关麽?”井邯很是惊惧,若真与先皇之死联系上,那可真是死有馀辜了。
“先皇醉心于长生之术,胶济王投其所好,先後将几名东海方士送入宫中为先皇秘炼长生丹药。後来,先皇暴亡,那几名方士都不知所终。今上即位之後,胶济王也曾经要送方士入宫,皆被今上婉拒了。父亲,我隐隐听说……那些丹药有毒!”
“啊……”井邯的声音有些颤抖,又有些急迫地问道:“此事当为宫廷秘闻,不可为公诸于天下,道听途说耳。那胶济王可宣之于朝野的罪证究竟为何?”谋反是重罪,总不能莫须有吧?